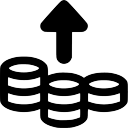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看到我母亲早上在太阳醒来之前化妆。通过起居室里的人造光线,她将镜子紧凑地贴在脸上,用唇膏勾勒出嘴唇的线条。她将它们扯了一次,两次,然后用唇膏轻轻地划过她的脸颊,用指尖将它混合到她的皮肤里,将厚重的条纹变成像魔术师一样的玫瑰色光芒。当她完成后,她将她仍然潮湿的头发翻过来,然后在加热器前挥动片刻。然后我们出门了,就像太阳开始升起一样。

我父母在我两岁时分手了。我的母亲把我带走了,将她的一半房子卖给了我父亲,用这笔钱购买了一个适度的公寓,就这样,我们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独自成了两个女孩。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即保持灯光和热水的运行。我对她的回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女人在财务独立方面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那时候,我的母亲比我现在年轻。还没有三十个已经离婚,还有一个小孩,她回到学校获得大学学位。当钱不足时,她带我去和她一起讲课,在那里我尽职尽责地坐在她身边,默默地抽出时间来打发时间。当她开始全职工作时,她也会这样做 - 但是,我会坐在她的桌子下,时不时地出现在她的复印中,用我手上的十一亿张复印件进行复印。在晚上,她给我读了书,在我上小学之前,她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她制作的抽认卡进行阅读和写作。
我不认为那时我意识到她一定有多难,因为她的不可动摇的移民姓氏的固有障碍(在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仍然主要是对南欧移民的敌意),并且是一个单身母亲进入劳动力基本上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说“谢谢” - 当时,我很难理解她的决心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明白在她面前的任务看来是多么不可能。
当我们谈论讲故事时,我们经常说“表演,不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母亲向我展示了如何在银行里自己赚钱的女人。当她的婚姻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成功时,我看到生活会变得渺茫。在她对一个小小的,贫困的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时候,这种意想不到的扭曲使她的生活陷入混乱。
我看到她追逐她想要的东西,即使世界似乎说“不”,并且孜孜不倦地坚持不懈,努力工作,她可以付出代价让我们吃饱,温暖,穿上衣服。最后,她会见到我的继父并再婚,然后我会再看一遍 - 我会看到她保留自己的储蓄账户,当他的收入足以支持她时,我看到她拒绝给予她自己的工作,到今天她仍然做兼职。
我母亲告诉我,你可以依靠唯一的人来获得经济支持。生活是不可预测的。我祖母一代人依靠的收入更是如此。她告诉我,社会中唯一的答案,就是女性,母性和种族制造困难的文化观念,就是证明他们是错的。她教会我,你有时可能会失败,而且可能经常会受到伤害,但你会重新站起来并一次又一次地做到这一点,直到某事给定。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我感到“生病”的时候,她曾经强迫我上学或上周末的工作。
“妈妈”,我从卧室打电话给她,“我感觉不舒服,我觉得我不能上学。”她几乎立即出现在门口。
“它是什么?”她会问,拖着她的手在我的额头上休息以感受到热量,“你死了吗,我们需要赶紧去医院。”

“不,没有那样,”我羞怯地说。 “我的喉咙有点沙哑。”
“好吧,”她回答说,“如果你没有死,那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未错过上学或工作的那一天。
“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我的妈妈会说,“艰难的事情发生了。”她告诉我,要在智力上和经济上独立,我必须无法满足。她还告诉我,所有的工作 - 无论是我在15岁时的表格,还是像25岁那样为律师工作 - 都是光荣的工作。她从不让我因为流鼻涕而退出服务行业工作,因为正如她所说,“无论是什么,你都必须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但正是那些形成时期,当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时,它才是我们两个人。
在清晨,沿着荒凉的街道行驶,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房间里的门廊灯光熄灭,太阳照在城市天际线上,妈妈会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 “赛车手,”我会说,“但那是不可能的。”
当她回答我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她的额头总会皱起眉头,经过短暂的停顿,“什么是不可能的?”
“没什么,”当我们开车进入阳光时,我会回答。